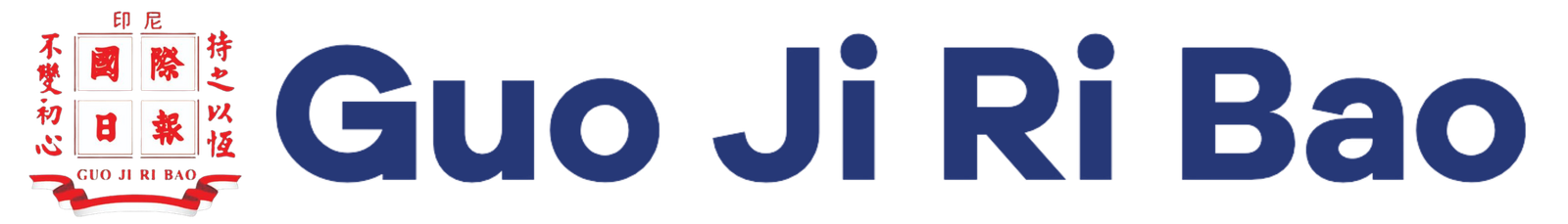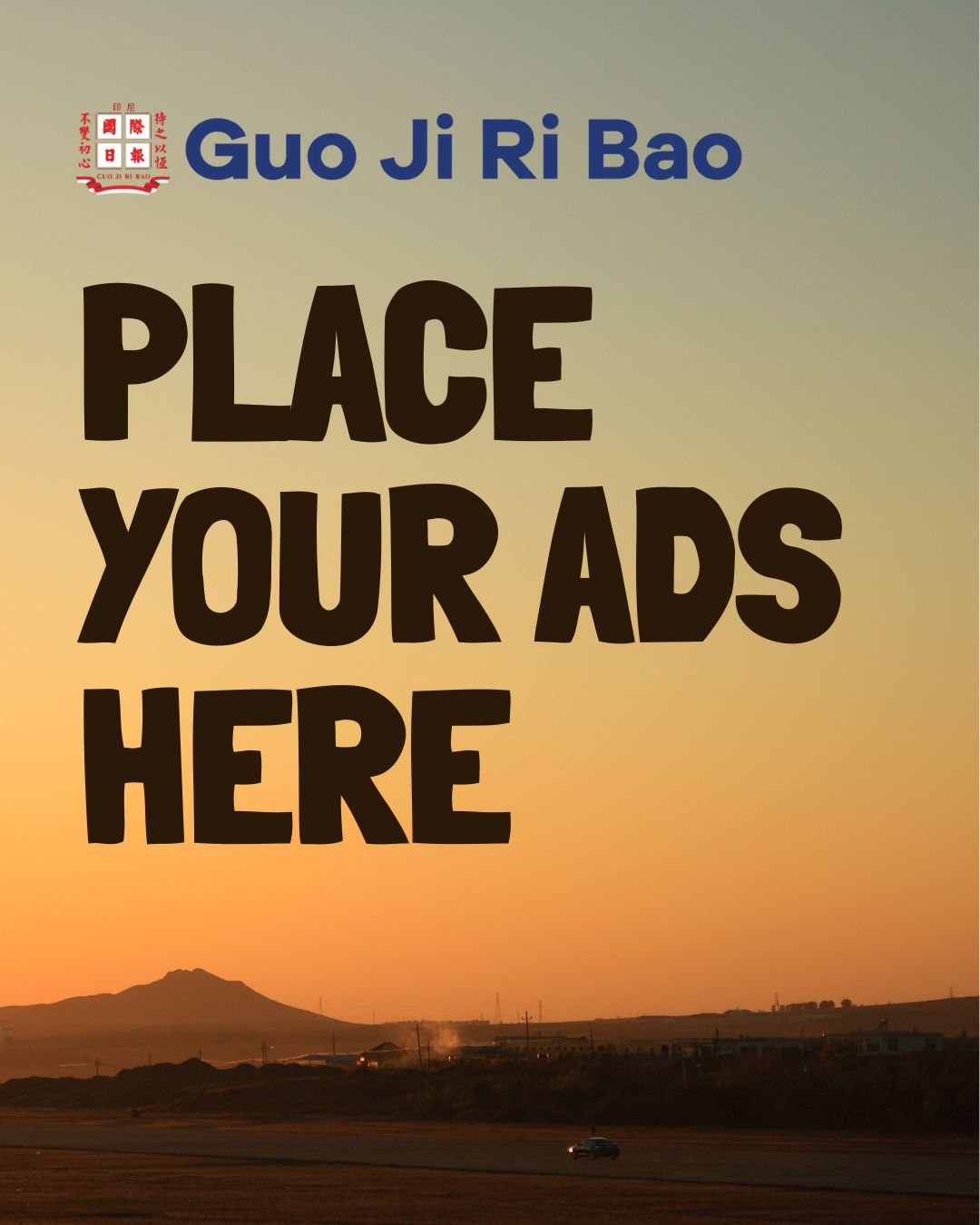陈烨 (博士)
去三宝垄之前, 我曾偶然买到一盒印尼饼干,包装上印着 “TRAVEL JAVA
TENGAH 2013″ —— “2013中爪哇旅游” 。这行字悄然没入心底,仿佛一个轻盈
的邀约, 在我忙碌的教学生活中种下了种子。于是那年4月, 趁着 Good Friday
连同周末凑成的小长假, 我第一次踏上了前往中爪哇首府的旅程。印度尼西
亚有许多这样悄然而至的假期, 为寻常的周末镶上一道金边, 也让旅人得以从
容出发。
真正走进三宝垄, 才明白这座首府城市为迎接游客所花的心思。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 是那时刚刚启用的 TRANS BUS SEMARANG —— 三宝垄穿梭巴士。
乳白色的车体流线型而现代, 线路从北到南、自东往西, 如血脉般贯通全城。
站台高出路面约一米, 与车厢踏板平齐, 仿佛专为从容上下而设计。 每隔约
500米就有一站, 每隔十来分钟就有一班。我递过3500卢比,售票员微笑颔首,
我于是从大太阳下得以窝进软座, 享受冷气, 静看市景流动。
若在其它国家, 这样的公交系统或许不算什么。但在2013年的印尼, 街头
大多仍跑着嘈杂闷热的 Angkot (小巴) 和老旧大巴, 能搭上这般洁净、舒适且
票价亲民的巴士, 就是一种小幸运。
三宝垄市区不大, 尤其适合步行探索。我沿着街道信步, 来到市中心的大
圆盘, 六条大道于此交汇, 环绕着市政厅、酒店、教堂与军事博物馆, 中间是
圆形的一个花园。Lawang Sewu 是最具特色的一个建筑物, 远望仿佛一座宏大
的教堂, 尖顶拱窗, 气势犹存。它在印尼语中意为 “千重门” , 原是一处荷兰殖
民时期的铁路枢纽站, 现在是荷属东印度铁路公司总部旧址, 该建筑有342扇
门, 具有欧洲古典风格和爪哇本土特色。Lawang Sewu 现在是一座铁路博物馆
。走进去,才知糖业与铁路曾是它的心跳。荷兰人为运送糖料建造铁路, 于此
设立中心枢纽,成千上万的门扇穿梭其间,因而得名。 博物馆甚至贴心地为游
客准备雨胶鞋, 可踏下地下室, 亲历往日铁路遗存。 数百年过去,运糖铁路网
早已被更多现代车站替代, 但这座荷式建筑仍静立原地, 如一位沧桑却不失庄
严的老者。
离它不远, 还有一座被绿树掩映的古典建筑。我问站岗的警察, 他热情地
告诉我那是一座教堂, 并示意我可从小桥绕进。我踱步而入, 只见教堂外摆满
白色椅子, 堂内有人正在精心插置鲜花。我悄悄坐在后排长椅上, 仰望耶稣圣
像, 才恍然想起这正是复活节前夕。空气中有一种宁静的喜悦, 仿佛透进来的
光线都格外慈悲。
而若论及三宝垄的信仰图景, 则绝不能略过 Sam Poo Kong————三宝庙
。 三宝垄的华文名称正源于此。它是为纪念明代航海家郑和 (原名马三宝)
而建。在我看来, 唯有 “红、大、雄” 三字才堪形容: 红墙环抱、殿宇宏阔、气
象雄浑。郑和铜像矗立其间, 身着明代官服, 一手持望远镜, 一手执剑, 目光如
炬, 望向历史的远方。我到访那天恰是周六, 大殿前正上演舞龙、狮舞, 甚至
还有改编的《江南Style》和印尼传统舞蹈。游客聚坐凉棚下, 喝彩不绝。天宇
湛蓝, 白云流转, 映得整座庙宇愈发鲜艳灼目。
整座印尼群岛, 无人不晓三宝庙。它始建于15世纪, 由华侨与本地人合建,
纪念郑和1405年率队抵此开展贸易。建筑依山面海, 融合中式古庙与南洋风
格。庙门悬 “三宝圣祠” 石匾, 琉璃瓦金灿耀目, 石狮与华裔石像分立两侧。庭
院涵括福兴庙、船舡爷庙与古墓园, 中心的 “三宝洞” 供奉郑和全身像及一口
古老的三宝井, 相传取水可祈愿得福。这里不仅是文化遗产, 更是无数华侨的
精神原乡。每年农历六月十三, 相传是郑和登陆爪哇之日, 此处都会举行盛大
庙会, 中印尼文化于此交汇,代代相传。
另一处让我留连的, 是三宝垄的老城区 (Kota Lama) 。石砖铺就的窄街, 殖民
时期遗留的建筑, 东正教教堂里正举行弥撒, 墙壁斑驳间却可见工整涂鸦 ……
时空在这里交错。我尤其难忘那家叫做 “Ikan Bakar Cianjur” (简称IBC) 的烤鱼
店。店内混搭中国与印尼风情: 青花瓷盘嵌作墙饰, 大水缸置于中央, 陈逸飞
风格的古典红衣女郎画作悬于墙面, 老式潜水装备静隅展示
———————— 仿佛一座微型的民俗美术馆。我连续两日来此用餐, 佐以
特调酱汁的烤鱼, 吃得心满意足。
IBC 餐厅旁矗立一幢纯白的大洋葱顶的欧式东正教教堂建筑, 据说是印尼最
早安装电梯的楼宇, 如今已作保险公司之用。整片老城区域仿佛不愿追随时
代脚步, 执意停留在某个旧日频道。它凝萃了荷兰与印尼的建筑语汇, 残旧中
自带贵气, 市井中不乏文艺。穿行其间, 恍然不知身在何国何年。它不刻意修
缮, 却反而保留下一片可触的历史温度。
我下榻在 Imam Bonjol 路一带, 不远处便是三宝垄当时最新、最现代的购
物中心 —— Paragon Mall。一楼的星巴克以咖啡渣拼出中国地图, 令我顿觉亲
切。商场人流如织, 恍惚间我仿佛回到上海。书店、音像店、箱包店一一逛
过, 最后走上四楼美食广场, 点一份冰饮与简餐, 倚窗而坐, 疲惫也随之消散。
但三宝垄最打动我的, 还不是这些风景, 而是它流露出的 “善” 意 ————
文与雅之外的第三宝。记得2013年那天我从井里汶乘火车抵达时, 已是深夜
11 点半。旅馆老板却主动来车站相接。电话接通那一刻, 他竟用中文唤我的
名字: “陈烨, 你在哪里? ” 令我惊喜交加。这位与我年纪相仿的房东, 一路开
车一路如数家珍地讲解这座城市。归程那天, 他再次发讯息来问火车时刻, 执
意送行。途中他特意绕经唐人街, 指着一座小庙说: “在印尼, 凡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庙。”他的母亲就在那附近经营一家小小的针线铺。言语间尽是平淡,却
道出了文化扎根的深远力量。
2025年7月, 我重返三宝垄。依然选择住在老城, 这一次入住的是一家充满
历史气息的酒店。依然每天步行至IBC烤鱼店吃饭, 依然重访三宝庙与商场。
十二年过去, 这座城市并未有很大的改天换地, 楼未增高、路未扩宽, 却更显
从容。老城区域做了细致的改造, 却仍保留那些斑驳的砖墙、锈蚀的窗棂, 不
舍得磨去所有的岁月痕迹。
与三宝垄的相遇和重逢, 如同一场与 “名媛” 的再回首, 她并未因时光流逝
而褪色, 反而因自信与沉淀, 更显气质。她从容展示每一处角度的美: 既有昔
日的涵养与品位, 也有未来的格调与潜力。
我轻轻而来, 又悄悄离开。挥别之际, 眼中所映、心中所念, 仍是三宝垄那
三宝: 文、雅与善。它的 “文” , 是千重门博物馆里的铁轨记忆, 是三宝庙中的
香火绵延; 它的 “雅” , 是旧城楼宇间的殖民低语, 是烤鱼店中青花瓷餐具与南
洋风味的交织; 而它的 “善” , 是火车站一句乡音般的问候, 是唐人街角那盏永
不熄灭的庙灯, 是一位普通旅馆老板的温暖相待。
我来过, 又离开。但我知道, 三宝垄的文、雅与善, 从未随岁月流逝。 它静
立于中爪哇的海滨, 如郑和的目光一般, 永远望向远方, 却始终坚毅又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