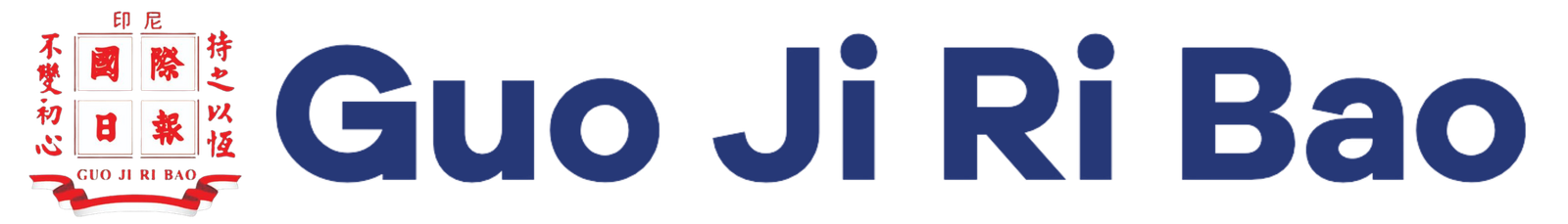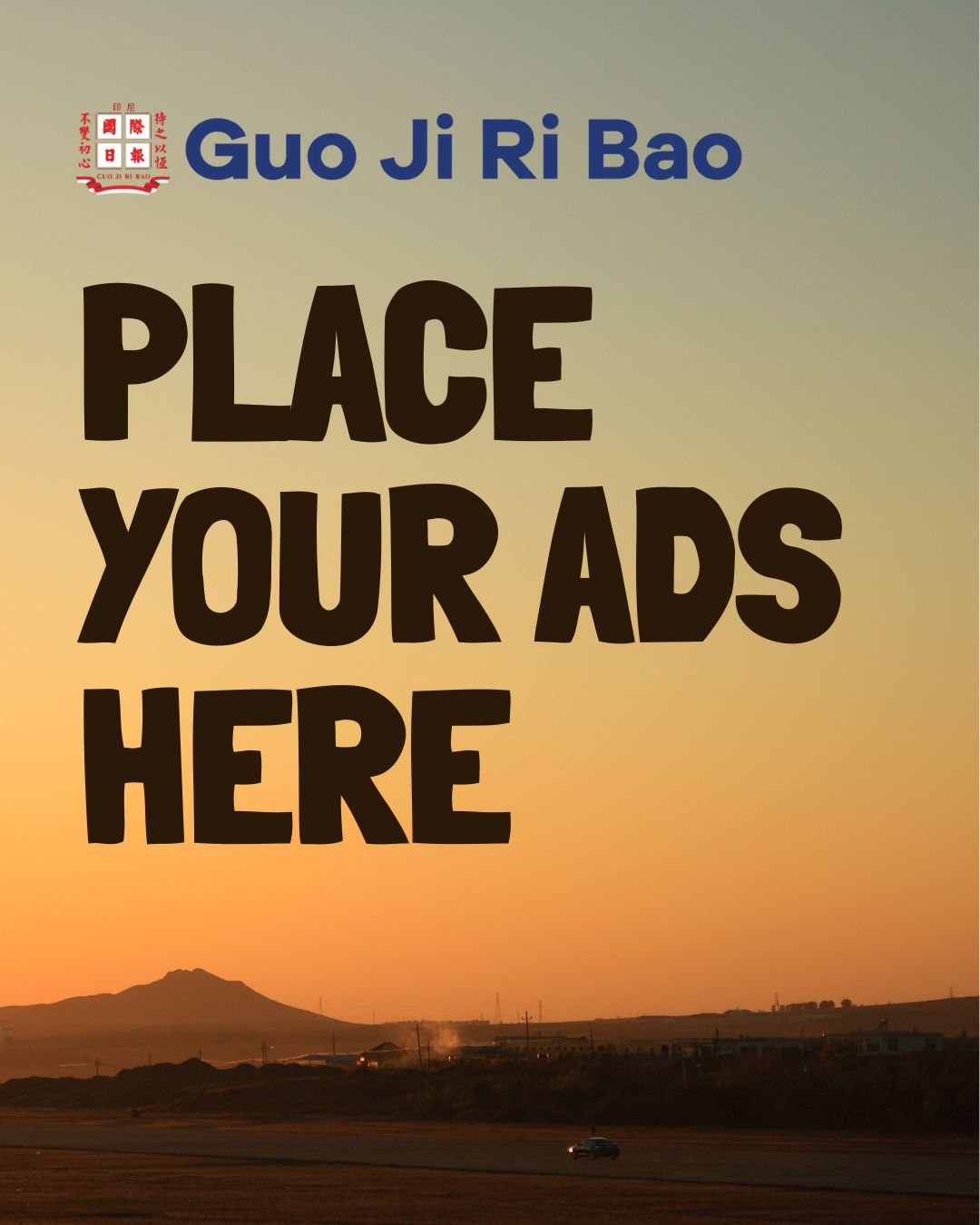贾俊英
得知李卓辉先生仙逝的消息时,我久久无法平静。这位被印尼华社尊为“Matahari Pendidikan Tionghoa”(华文教育的太阳)的前辈,于我而言,既是印尼华商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相知甚深的忘年之交。十余年间,从厦门大学初遇时他伏案疾书的执拗身影,到清华园中的畅叙,再到每周雷打不动跨越重洋的华文报刊定稿电邮,他的音容笑貌与精神风骨,早已镌刻在记忆深处。谨以文字梳理先生的精神遗产,既是对逝者的告慰,亦是对生者的激励。
先生的一生角色多元,报人、教育者、学者三重身份交织,共同勾勒出一位华人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开拓。
笔耕不辍:风雨报途守文心
1938 年生于印尼的李卓辉先生,祖籍福建南安,自幼浸润于中华文化。1960 年初,他受邀加入印尼最大报业集团《新报》,担任华文版《忠诚报》执行编辑与主笔,其秉持的以 “立足本土、兼顾华社” 的报人视角深受读者信赖。1965 年政局变动后,华文报刊与华校遭禁,他的报业生涯被迫中断,但笔耕之志从未熄灭。
此后二十余年,先生在西爪哇勿加西的德固纸浆造纸厂担任厂长,系统接受现代企业管理训练并获管理硕士学位,期间考察欧美日及两岸纸浆工业的经历,更让他练就了跨文化观察的敏锐视角。2015 年先生带我参观工厂旧址时曾坦言:“机器运转的轰鸣声里,总想着华文报刊的版面编排。” 他在这一时期悄悄积累的印尼政治与华人历史研究笔记,后来成为其论著的重要素材。90 年代中后期先生涉足家电代理行业,1998 年暴乱中商店被毁、被迫流亡期间,仍应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之邀撰写印尼时局评论,以笔为刃记录华人社会的阵痛与抗争。
2001 年先生应召返印尼出任《国际日报》总编辑,坚持每日撰写社论,其 “以事实为基、以公理为尺” 的评论风格,使该报成为华社发声的重要平台。2012 年任印尼《星洲日报》主笔,2013 年创办《巴厘风采》,2014 年再创办《印华日报》,在全球报业式微、运营持续亏损且无报酬的困境下,仍坚守 “华文报刊是华人社会的精神灯塔” 的信念,直至晚年仍亲写社论。这种 “不问盈亏、只问传承” 的办报精神,在数字媒体冲击的时代更显珍贵。
薪火相传:跨族教育架桥梁
20 世纪 60 年代初,李卓辉在印尼华文教育的黄金时期踏上教坛,担任华文中学初高中教师,在课堂上系统传授中文知识与中华文化,成为许多华人子弟的启蒙者。1965 年印尼政局变动后,华文报刊与华校被迫关闭,他的公开教学生涯戛然而止,但教师情结贯穿终身。
“房子可以卖掉,但中文不可以不读”,这是先生家中坚守的信条。他与太太贺晓玲坚持让五个子女打下扎实中文功底。先生曾十分动情地对我说:“传播中华文化,要从我和我的孩子做起”。如今两位女儿在华文教育领域颇有成就,外孙女李华丽也曾协助其办报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先生曾欣慰地说:“这是中文教育给孩子的礼物。”
先生的教育视野从未囿于华人社群。2011 年,他与梁世桢、沈德民博士等倡议创办东盟南洋大学,推动区域文化交流;2017 年力促东盟南洋基金会与印尼最大温和伊斯兰组织伊联合作,在伊联大学设立 “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开创宗教机构与华文教育合作的先河。通过伊联旗下 3 万所中小学的网络,华文课程得以走进印尼主流社会。他还促成伊联大学与广西民族大学的合作,每年选派印尼学生赴华深造。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印尼研究中心的顾问,先生不仅捐出珍藏的侨史文献,更私下资助数十名家境贫寒的华人与原住民学生赴华深造。他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教育不是圈地自守,而是搭建桥梁的基石。” 这种开放的教育理念,打破了族群与宗教的壁垒。
著述等身:构建印华研究体系
先生的四十多部著作构建了其印尼华人研究从碎片化记录到系统化学术的框架。《印尼华校精英风雨沧桑》系统梳理华校兴衰与教师群体实践,填补了印尼华文教育黄金时代与断层期的史料空白;《印华先驱人物光辉岁月》以企业家、教育家的生命史为线索,梳理了华人从 “侨居” 到 “定居” 的身份转变轨迹,展现中华文化与印尼本土文化的调适过程;政论集《大江浩海 印华风雨》展现 1998 年民主改革后华社的政策博弈和族群关系演变;经济维度则聚焦林绍良等侨商在印尼工业化与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双重角色,揭示华人资本 “双向中介” 的独特功能。
整体而言,先生的研究从早期以教育史为核心,逐步延伸至政治、经济、媒体等领域,覆盖从殖民时期到当代的完整历史脉络,形成综合性研究体系。先生在多个场合强调:“历史记忆是族群存续的根基”,他的学术实践正是这种记忆最珍贵的载体。
育材不倦:无私托举后辈学人
先生常对后辈学人 “授人以渔”,无私提携。我与先生的缘分始于厦门大学《印尼 < 生活报 > 纪念丛书》发布会,彼时他虽事务繁忙,但仍接受我的访谈邀请,并明确提醒我要“深入华人社会”。此后我多次前往印尼调研,先生的帮助细致入微:提前联系侨社领袖、资深报人等访谈对象,亲自陪同前往印尼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查阅20世纪上半叶的档案和报刊,协调雅加达和万隆的私人藏书机构向我开放侨史特藏。2015 年调研结束时,他将早年收集的侨刊、老照片等珍贵资料悉数相赠,还联系物流企业将数百本华侨华人研究文献妥善运回中国 —— 这些资料后来成为我《印度尼西亚中华商会研究》项目的核心实证。这些年每周收到的华文报刊电子版上,常有先生的社论。先生的《华社路在何方?》至今仍是我的案头常备。“俊英啊,要多写多出啊”“俊英啊,要来印尼啊”—— 微信通话中这些朴实的叮嘱,既是师长的教诲,更似长辈的牵挂,让我倍感温暖。
先生虽逝,但其以笔为犁守护华人话语权的报人风骨、以教为舟传承中华文化的师者情怀、以史为鉴构建华人研究体系的治学精神,已化作照亮印尼华人社会赓续传承与文明交融互鉴之路的不灭灯火。
李总,文光永耀,一路走好!(作者贾俊英是华中师范大学印尼华商研究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