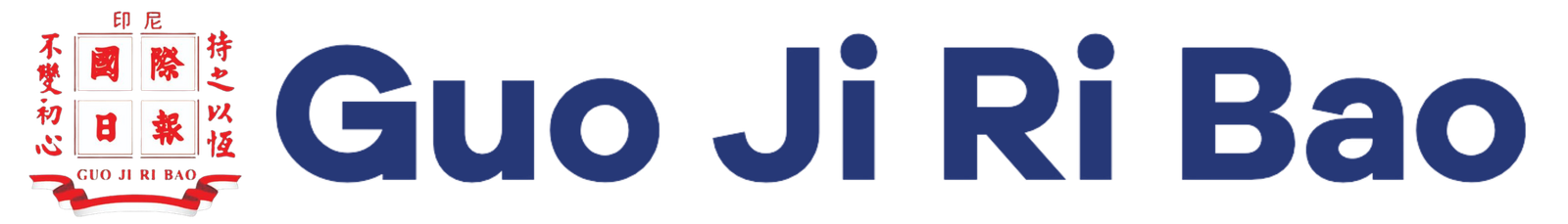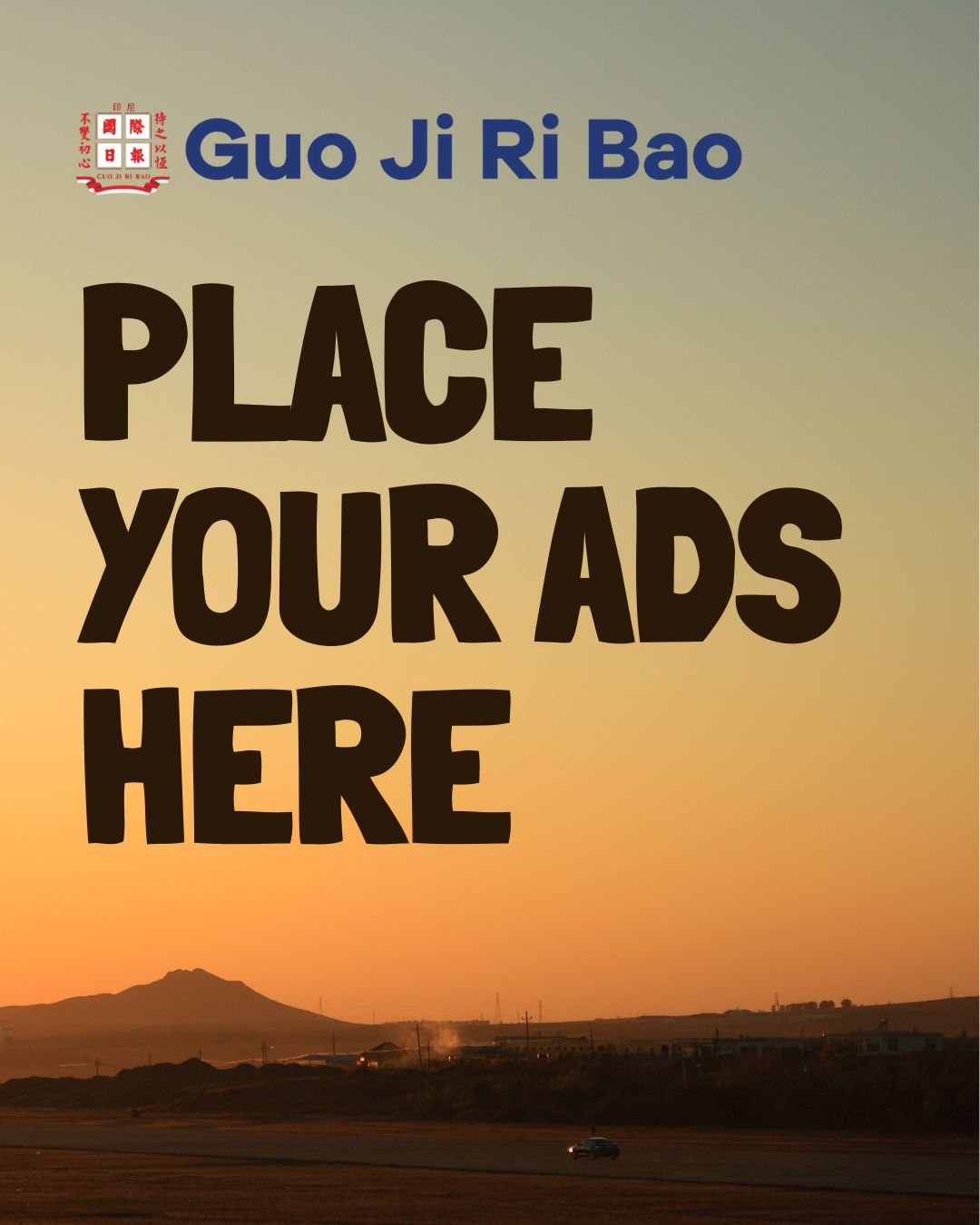藏在东南村8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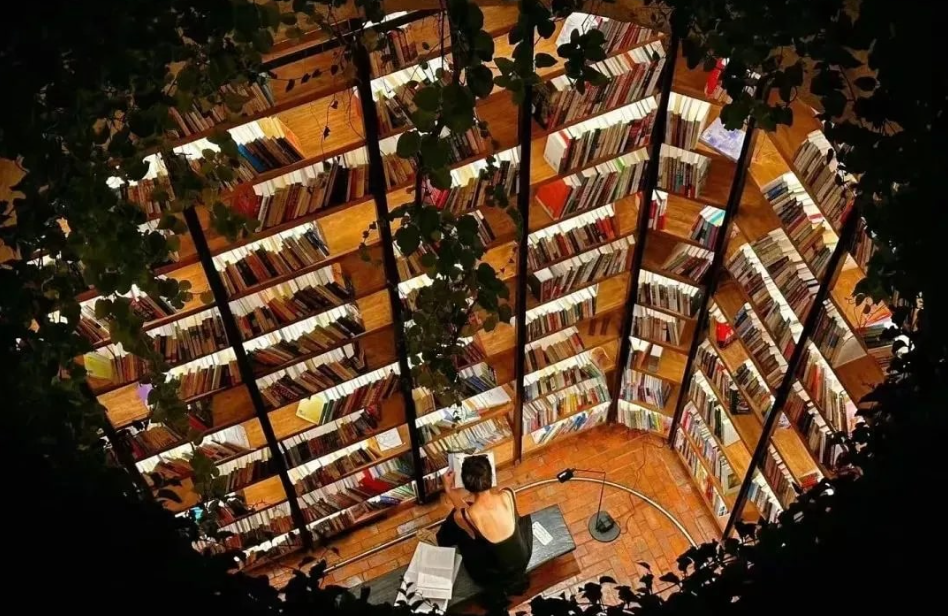
“在我心里,8号更像是一个容器,容纳来往者的生活,它承载了所有的可能性。我希望他是一个能够滋养和支持跟这个空间有缘分的人,有着无言的背景式的陪伴。”正因白惠泽的这个想法,“公共区域”成为了8号设计之初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加上白惠泽自己的房间,8号一共只有7间房间,然而有客厅、餐厅、院子、露台、树林、茶室、观景台;有营地、菜地、停车场……足足2000多平米的总规划空间,公共区域占了90%以上。6间客房匹配了极为丰富的场景,出发点就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他自在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8号空间设计的另一个情感动力点,则来自于白惠泽对朋友的投射。“我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人。比如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非常包裹的小空间,所以我们有一个房间的整个床就像小龛一样的。”同样的,有朋友在野外待惯了,喜欢开阔的空间,于是公共空间都是打通的大空间。每个人不管什么状态,什么性格,以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来到8号,都能以他自己的方式找到他自在的角落。
在白惠泽眼里,即便是过路人、朋友或是住店的客人,在建筑存在的周期内,都会留下他们的印记。即使到了15年、20年后,这个房子没有续租,它被交还给本地的白族房东,无论他们是否理解8号做建筑的初衷,是否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我们的房东的家人、后代,依然会从这座建筑中获得某种支持、影响、庇护或滋养。我认为,这正是8号存在的最根本原因。”
作为白惠泽的朋友和8号的共建人,蒲熠星经常来8号小住,每天睡到自然醒,中午去镇子上觅食,沙溪就像一个游戏中的补给村落,村里有很多“NPC”,每个人都擅长一些独特的技能。身怀“绝技”的居民里,会“做饭”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技之长了。整个村子周围,“埋伏”着许多擅长做饭的店主,他们是最早一批来到沙溪的外地人,被大家称为“老沙溪”,也就是白惠泽的一群好朋友。很多人曾在世界各地做过背包客或沙发客,游历了许多地方后,觉得沙溪非常符合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方式,于是决定在这里定居。沙溪有一家汉堡店,老板最近又开了一家披萨店,他是“老沙溪”中最勤快、最爱赚钱的人。在蒲熠星眼里是他在全世界吃过的最好吃的汉堡。吃完在镇子里散散步,等到太阳下山了就变冷了,就回8号喝酒看星星。他最初来到沙溪时,经白惠泽介绍遇到了“胡子哥”,晚上就一起喝酒,围着篝火弹琴唱歌这种。白惠泽还在书塔的露台砌了一个小澡池,朋友们可以一起泡澡。大家一起打游戏、聊天,烤烤火,一种宁谧的日常状态。“平常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每天都像是身处生死关头,感觉像是在打仗。所以我来8号,是为了从日常现实中抽离出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在内心获得宁静,也有一些时间创作。”忠实“住客” 蒲熠星说。
8号的整个架构的准备非常简单,除了固定“NPC”白惠泽之外,还有两个本地的大理阿姐负责所有的空间卫生、布草。2025年理想情况是还将有一个义工,白惠泽希望给更多想在大理沙溪作深度停留,想要和接触当地文化的人提供落脚点。
在世界兵荒马乱的当下,空间结构、生活方式、甚至个体性格,都可以是温柔浪漫的。浪漫的生活似乎是白惠泽的精神状态里“长”出来的,8号在社群中更加贴近“民宿”的古典的概念:住在当地民居里跟主人产生生活上的交互,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一起放松,攀登有着深深岩石影子的锥子山、寻找山坡上半圆的小泉井、采摘石榴树将开未开的火红花骨朵。而在蒲熠星眼里:“我参加了很多节目,大部分是脑力综艺,似乎很多人觉得我是从理性出发的一个人,但我现在逐渐意识到对世界的感知可能更重要。8号的出现的刚好承载了我这方面需求。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
沙溪地处南北两个垭口之间,澜沧江的第二大支流黑惠江贯穿整个坝子,是沙溪的母亲河。小镇东西两侧则被弯曲的山脉环绕,形成了“两山夹一水”的地理格局,山水之间的通行非常方便。整个坝子从最远的村落到8号,最多不过四五公里,这样的距离在城市中是难以想象的。沙溪是白族、彝族人的聚居地,白族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白族人勤劳质朴,他们的建筑、服饰、饮食和节庆活动都充满了独特的民族魅力。
生活在沙溪的本地人,一生几乎都在这片小小的坝子里度过,白惠泽分享,在沙溪住一段时间后,可以感受到“身边的附近”和一种“浓缩的世界”。花园和草地的幽静不用看,光“听”就显得圆满有生机。居住在沙溪的这5年间,他不断地有新的感悟和灵感,他对当地人文、四周邻里、自然和生命的感悟元素得以在房子里生长。他理解了人与人的赤裸的真诚与亲近,感受到了“天似穹庐”、时间是圆形的周期性的,自然和生命的体悟随之产生。“每一天,我都会自然而然地关注身边的一切,随着注意力的变化,我们的体验和感知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感受到身体的空间的选择,也能意识到像伊本·白图泰的诗歌写的“远行,让你一路沉默无言,再把你变成讲故事的人”,远行至此,在此地安家,自己也成为故事中的人。
蒲熠星不自觉地也成为了讲故事的人。白日休憩,四处闲逛,兜兜转转绕进当地院落,行至半途的时候,听见楼顶有一阵古筝。“他弹得实在太差了,不是很悦耳的。”他好奇地登高一看,发现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大爷在那里练琴。大爷专拉二胡,“为什么今天在这儿练古筝?”作为茶马古道重镇,沙溪四方街的兴教寺保存完好,茶马古道的遗迹依然可见。古镇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路边的店铺虽已不再是当年的马帮茶馆,但依旧保留了浓郁的历史气息。兴教寺与四方街是古镇的核心,在这里,时间仿佛凝固,游客可以触摸到那个古老商贸时代的脉搏,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庙,既是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教科书。兴教寺的古戏台,木质结构精美,雕梁画栋,历经数百年风雨仍然保存完好。这里不仅承载着宗教仪式,也见证了无数场民间戏剧的上演。如今,古戏台依然时常举办活动,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的窗口,展现本地文化生活。戏台旁边有魁阁,古代的科举制度和庙宇文化互为依托,庙内的第二进院常用于演出,展示的洞经古乐据说源自唐代以前,是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在沙溪本地,有一个老年人自发组织关于洞经古乐的民乐团,乐团成员全是年逾八旬的老大爷老奶奶——这个大爷便是民乐团的二胡手。他的好友原先弹古筝,可惜去世了,他便拿着好友生前的遗物古筝练习。乐团是人均年龄八十几岁,所以这几年老人们也在陆续地走,乐手没有传承,二胡老大爷主动联系古筝大爷的家人,把古筝买过来,友情如此很明确很强烈,怀抱遗物,大爷就从零开始研学,弹出生疏的筝声。“后来我们就没有碰到这个大爷了。”经乐之外,白族地区文脉浓厚,包括剑川的楹联文化与国画传承,村子里随随便便就能找出来写得一笔好字的老先生。东南村8号的房东一家也是如此,房东的儿子都是写书法画国画的,老先生把他写的诗非常兴奋地给大家阅读分享。“和老人家一起读诗,我们就几个人坐在那很惬意。”说起这些故事,白惠泽和蒲熠星依旧眉飞色舞,经历过的故事在那个夏日被短暂地烧化了,又在雾气里等待下一张面孔聆听。
8号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似乎宏观来看,在世俗社会中,人如果过多地表达自己敏感、痛苦,或者对精神需求的追求,往往容易被认为是一种脆弱。
然而,群山环抱,好友在侧,繁星如同在骰筒里摇晃般跳脱天际时,我们知道,目的地对情感需求的满足,依旧是珍贵和不可或缺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