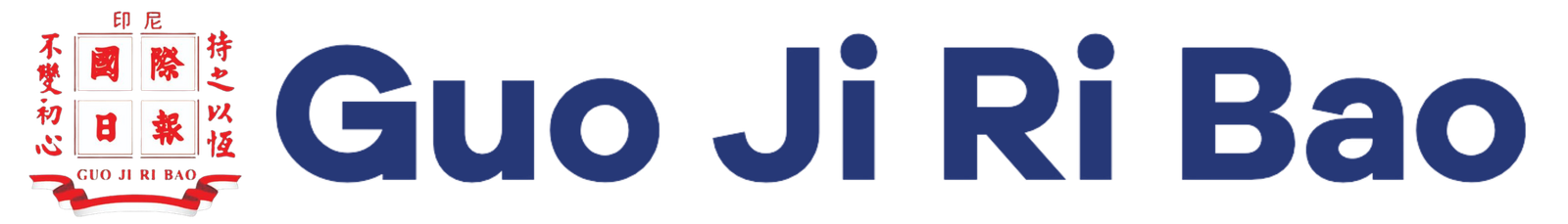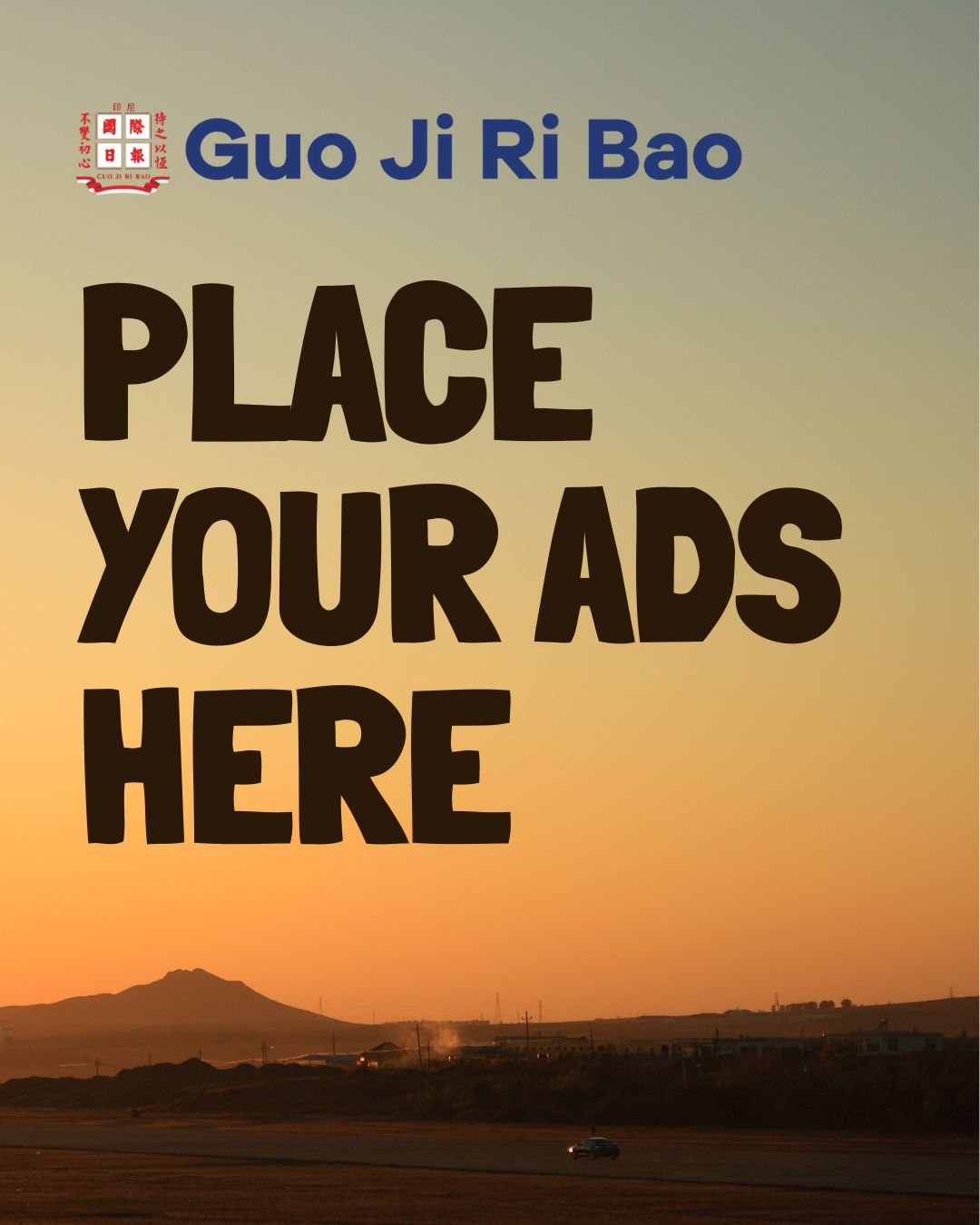我是一个潮汕人,祖籍故乡在广东揭阳县的「靛行街」。历史上,揭阳与潮州、汕头同属一个潮州府管辖的区域,三地在民俗、饮食后、宗族文化方面,都相差无几,称得上是「同源同宗」的关系,所以揭阳人自然被纳入「潮汕人」的范围。来揭阳由县升格为市,从此与汕头、潮州,分别成为三个平起平坐、行政互不隶属的城市,但语言文化仍属于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因此广义上仍然被看做是「潮汕地区」。
我儿时的老家,住在揭阳榕城的靛行街。
为什么叫「靛行街」呢?
因为这条街早年间满街都是做蓝靛染料的店铺。
「靛」是一种深蓝色的染料,是从一种植物叶「菁」提取出来的。那时候,织布作坊生产的布匹,还有老百姓家里自织的土布,都是白色的,需要用山里的草木捣制成一种蓼蓝作为染料,把这白布染制成蓝靛色的,才可以做衣服穿在身上。而我家居住的那条街,开了许多蓝靛染料店,清苦草木气,裹着榕江的水汽。
「靛」是一种深蓝色的染料,是从一种植物叶「菁」提取出来的。那时候,织布作坊生产的布匹,还有老百姓家里自织的土布,都是白色的,需要用山里的草木捣制成一种蓼蓝做为染料,把这白布染制成蓝靛色的,才可以做衣服穿在身上。而我家居住的那条街,开了许多蓝靛染料店,清苦草木气,裹着榕江的水汽,飘得整条街都是。街上铺的青石板路,长年累月被磨得又滑又亮,雨天踩上去不会沾泥。骑楼廊下,每天总聚着挑布担的商贩,还有寻染料的妇女来来去去,所以人们就把这条街叫做「靛行街」。
我少小离乡,对老家的印象已经模糊,依稀记得靛行街不甚宽阔,但建筑有序,铺户整齐,往时有「泰记」钱庄、盐厂、酱油厂、「红毛灰」。(水泥)窗制造厂等铺户,商贸繁荣。
老街不远处,有一条河,叫做北河,北河有个渡口,因靛行街得名,唤做「靛行渡」,有许多商船来往。靛行渡位于北河上游,在北河下游,紧邻榕城北门,还有一个火轮码头叫做北门渡,从前经过榕江,小火轮可直达汕头海港。我小时候跟随父母下南洋,就是从北门渡坐火轮到汕头,再乘漂洋过海的「红头船」出国的。
沧海桑田,人间巨变。如今靛行街古老的街巷早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河边大道,以及城市无处不见的高楼大厦,而靛行渡和北门渡也在大桥与高速公路四通八达之后,逐渐退出了航运舞台。只不过这些古老的名称依然保留,波光粼粼的江面,仍好像无声诉说着昔日难忘的历史。
百岁经历:“三国四地”六个朝代
1924年2月,我出生于广东揭阳县,那还是民国十三年的早春,寒风料峭。揭阳是粤东古邑,史载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广东省最古老的县份之一。我的老家在县城所在地玉滘村(后改名为榕城,现为揭阳市榕城区)的靛行街上。
写作这本人生琐记城的回忆录时,时间已是2025年的12月了。按照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习惯,我今年102岁,即将迈入103岁的门槛——确确实实属于“百万人中难得一见”的高寿了。
这一百年来,世界风云变幻,岁月起起落落。我作为从中国南来的第一代华侨,已亲身经历了“三国四地六个朝代”。所谓“三国四地”,是指我出生在中国揭阳,七岁时下南洋,先是随父母到马来亚砂拉越的古晋生活了两三年,然后又一路漂泊,流落到印尼西加的坤甸,在那里长大成家,四十多岁又来到爪哇岛的雅加达谋生创业,一直到今天。
所谓「六个朝代」,是指我小时候在中国,还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到了砂拉越古晋,当时的马来亚尚属于英国管辖的殖民地;后来到西加坤甸,起先是荷兰人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印尼落入日本人之手,前后占领了三年时间,然后日本投降,才宣布独立,从此进入开国总统苏加诺时代。1965年「九三〇事件」之后的32年,又变成苏哈多掌权的「新秩序」时代,直到1998年他被赶下台,印尼才进入「民主改革」的新时代。
如此算来,我的百年人生,漫漫长路,确实经历了「三国四地六个朝代」。虽然古人有言:“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身为凡夫俗子,我们在这大千世界,不过就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转瞬即逝。然而回首往事,堪称聊以自慰的是,不管任何时代,面对怎样的境遇,我们都曾摸爬滚打、挣扎奋斗,真诚生活,从未失去良知,也未停下前行的脚步。这期间也遇到许多大风大浪、艰难困苦,不敢说九死一生,却几番险遭灭顶之灾,大难不死,饱尝人间冷暖,世态炎凉。
在万丈红尘之中,留下的不只是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念想——念故土的炊烟,念他乡的灯火,念那些与我一同扛过风雨的故人,念这份在漂泊中生根、在动荡中传承的家国情怀。(未完待续。杨金锋口述,丁见记录整理)
揭阳榕城老城区有味道的骑楼建筑。

父亲杨墅亭与母亲郑丽真的遗照。

2020年2月20日,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肖谦在使馆会见为祖籍国抗击疫情捐款100万人民币的杨金锋老人,向他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