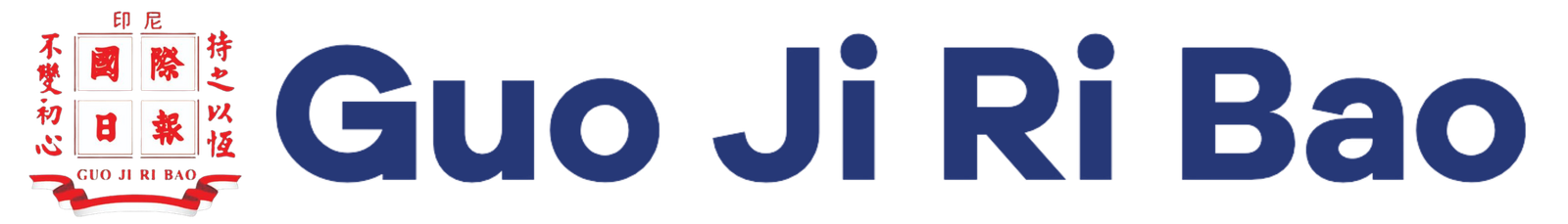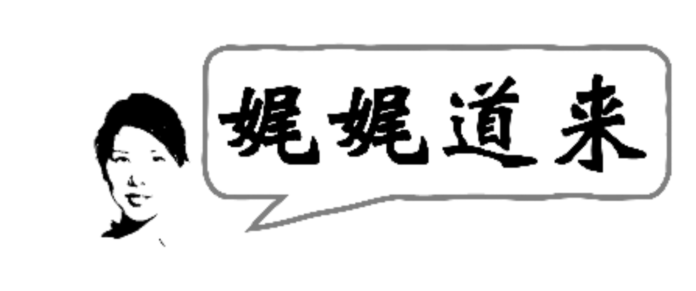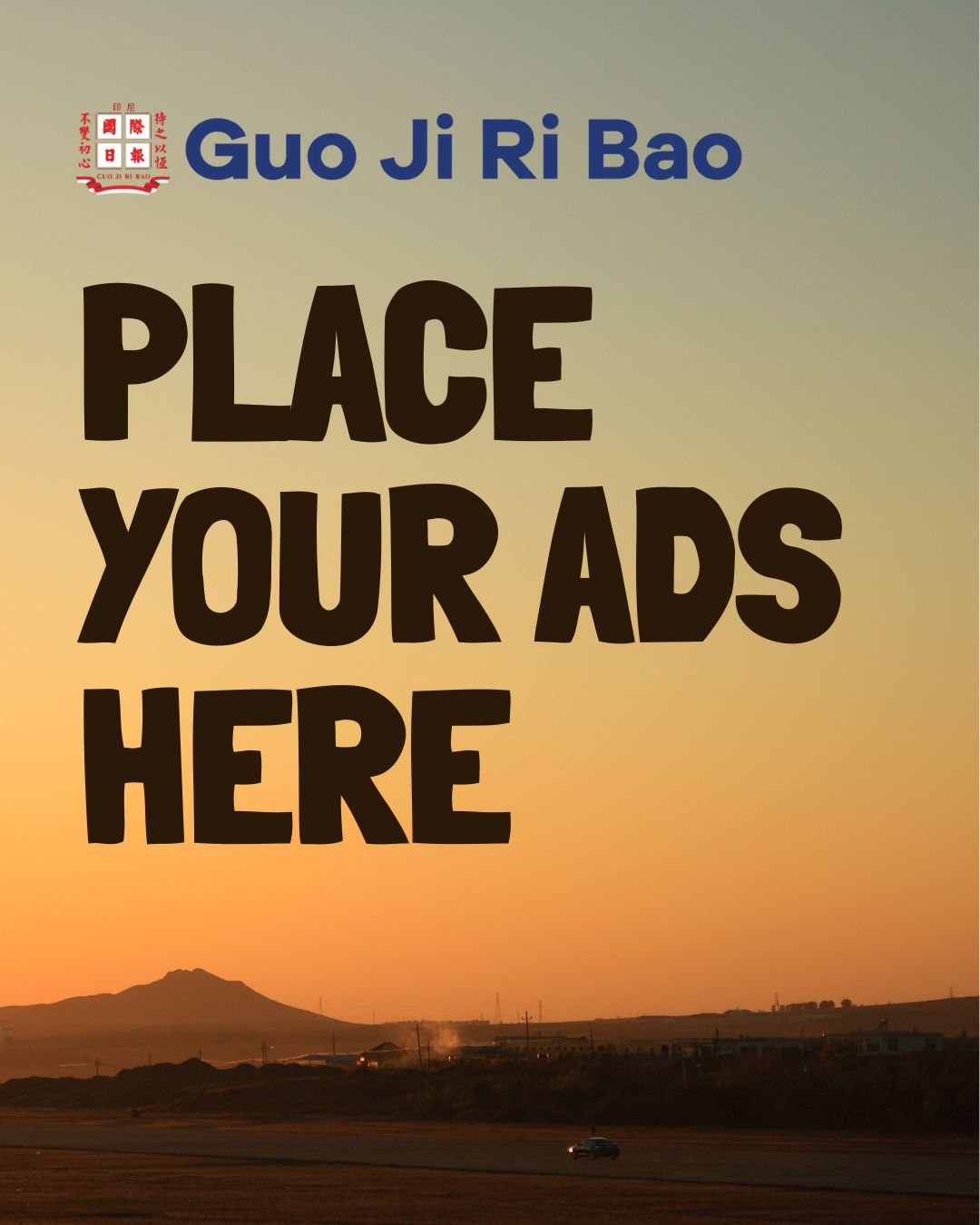宋娓
在今年5月初举行的“亚洲慈善峰会”上,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来到新加坡,宣布设立盖茨基金会新加坡办事处。这位微软联合创始人,尽管在2023年捐出了高达77.5亿美元,仍以1280亿美元的身家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七。而自基金会2000年成立以来,已累计捐出超过1000亿美元。
捐了这么多钱,为何比尔·盖茨仍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这背后的逻辑,并不是单纯的“散财为善”,而是一种成熟、结构化的现代财富管理方式。盖茨“捐”的,不仅是财富数字,更是对财富运作方式的系统重组。
迄今为止,盖茨基金会约41%的资金来自巴菲特,他个人已捐出超过430亿美元,其余基金主要来源于盖茨持有的微软股票等资产的增值。尽管巴菲特于2021年已辞去基金会职务,但基金会并非一个单一的慈善通道,而是拥有高度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架构。其资金由外部专业投资机构 Cascade Investment 负责运作,通过配置股票、债券、指数基金等多元资产,实现稳健的财富保值增值,同时持续支持全球公共卫生、教育、农业等关键项目。
虽然这些资产名义上已不归盖茨个人所有,但作为基金会的主席与受托人,盖茨仍掌握着投资方向和慈善战略的主导权。每年,盖茨基金会向全球多个领域捐赠数十亿美元,尤其在健康、发展与教育方面具备实质影响力,其对世界卫生组织及全球卫生政策的形成也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因此,盖茨并非是“舍弃”财富,而是通过慈善这种制度化方式,延展财富的公共价值,创造更持久的社会影响。
外界也曾质疑:盖茨是否借慈善避税?然而,美国税法对私人基金会的抵税额度限制相当严格:现金捐赠的抵税上限为收入的30%,非现金资产更低,仅为20%。据基金会官方数据,其过去25年的捐赠中,税务减免仅占总资产的0.8%至1.2%。如果盖茨的目标仅是减税,他完全可以选择让基金会长期运作、持续享受税收优惠,而不是设定在2045年之前支出全部资产,并永久关闭。这个决定意味着盖茨家族未来将无法长期控制这笔财富,反而要承担更高的执行成本和时间压力。
他曾表示,1889年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一书对他启发重大,其中那句“拥巨富而死者,耻辱”,成为他的人生警句。他不希望未来被世人记住的身份仅仅是“富豪”,而是一个“在有生之年完成使命”的行动者。他宣布将在未来20年捐出99%的个人财富,并将盖茨基金会在2045年前关闭——这比原先计划在他去世20年后关闭的安排大大提前。他希望通过加快捐赠进度,加速全球减贫与健康改善的进程。
这一决定背后,体现了盖茨的财富观与使命感,也反映出东西方财富观念的文化差异:华人认为,存下来的钱是属于自己的;而西方人则相信,用出去的钱才属于自己。正是在这种观念下,比尔·盖茨选择在有生之年完成捐赠,而非将财富留给后代或基金会长期控制。
在家族财富传承方面,盖茨也持有鲜明立场。尽管坐拥1280亿美元身家,他的子女却继承不到1%。他认为,过多财富会削弱下一代独立奋斗的意志与责任感。他希望传承的,不是金钱,而是价值观。财富“传家”不如“传世”:真正值得继承的,是影响世界的能力与责任。
比尔·盖茨并非孤例。“捐赠誓言”的另一位代表——沃伦·巴菲特,也早已承诺将99%以上的财富捐出。他曾说:“我会给孩子们足够的钱让他们觉得无所不能,但不会多到让他们什么都不想做。”他的子女未继承巨额资产,却获得管理基金会的责任。这种将“责任感”置于“占有欲”之上的传承逻辑,体现了一种更具未来导向的价值观。
在亚洲,也有企业家身体力行慈善。印尼国信集团创办人翁俊民,自2013年起与盖茨基金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双方各捐出1亿美元设立联合慈善基金,用于支持印尼公共卫生项目。这项合作不仅在当时的东南亚企业界引发关注,也被视为亚洲企业家主动参与全球公益协作、联动国际资源、推动国家公共健康体系建设的重要案例。
盖茨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基金会办事处,正是看中了其法治健全、资本开放、慈善生态成熟的环境优势。新加坡将成为盖茨基金会在全球的第12个办事处,意味着其对东南亚慈善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这不仅将促进与区域政府、公益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财散人聚,也可能带动慈善专业人才流向新加坡,加快建设“亚洲慈善中心”的步伐。盖茨基金会的全球布局与他个人的财富哲学,还将启发更多东方企业思考财富的意义和传承的价值。
回望盖茨的慈善实践可以发现:真正的富有,未必在于你拥有什么,而在于你愿意放下什么。水不流则腐,财不动则枯。财富若能走得比个人更远,善意若能通过治理并持续放大,方能体现持有者的格局,让财富在推动社会与文明进步的道路上,留下深远而有意义的印记。
(作者宋娓系新加坡《时代财智》总编辑)